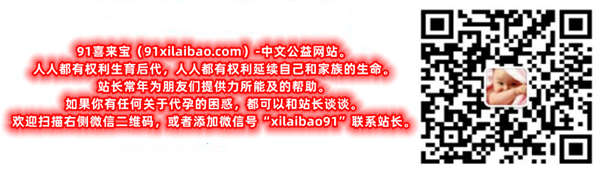从很多方面来说,《现在就全面代孕》(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并不是关于代孕本身。相反,该书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要求,即重组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因此,刘易斯加入了从自由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一系列女权主义者的行列,她们都将家庭视为不公正的目标(例如,米尔(Mill)1869 年的参考文献;乔多罗(Chodorow)1978 年的参考文献;奥金(Okin)1989 年的参考文献;库恩兹(Coontz)1992 年的参考文献)。然而,刘易斯的批判是专门针对同性恋、电子人、共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该书的标题等同于呼吁废除私有化的核心家庭。在刘易斯看来,"'废除家庭'指的是(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双刃胁迫的终结,在这种胁迫下,我们孕育的婴儿是我们的,也只有我们才能守护、投资和优先考虑"(119)。刘易斯的愿景是建立更多的社区家庭,并扩大而非破坏现有的关爱关系(19)。
一系列女权主义科幻小说中的一些例子说明了这种废除可能是怎样的。例如,在社会再生产中,性角色和父母角色将截然不同,公社中的孩子将不会被视为财产,抚养孩子的任务将由成年人平等分担(120-21)。这些建议部分针对的是人们对家庭是维持资本主义和财富不平等的机制的担忧(恩格斯参考资料 1884 年)。还有一些例子来自于另类家庭,如黑人、同性恋、变性人和移民社区,他们破坏了家庭的运作方式。例如,"mamahood"(妈妈的身份)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养育孩子是在没有支配或财产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152-53),以及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 "的格言(147)。在刘易斯看来,那些主流社会中的 "异类"--那些非异性恋、非白人、非顺式性别、非公民、非有产者等等--展示了以不同方式(大概)更好地组建家庭的方法。
刘易斯认为代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因此将其纳入了讨论范围。在这里,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电子女权主义者(例如,Firestone,参考文献 Firestone 1970;Haraway,参考文献 Haraway 1991)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女权主义者拥抱技术,如代孕中使用的试管婴儿和人造子宫,以完全接管孕育过程,将我们从狭隘的、压迫性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刘易斯也希望通过代孕来改变我们的家庭观念。代孕妈妈已经在挑战家庭的创建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未来: 如果代孕做得好,"将预示着真正的相互性"(167)。
然而,重要的是,刘易斯并不希望出现更多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中存在的同类代孕现象,帕特尔医生的阿坎莎不孕症诊所就是其中的典范(第 3 章和第 4 章)。相反,刘易斯提出了一种 "超越认知"(33)的代孕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们都以多重角色参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以孕育者为唯一角色的私人再生产。刘易斯认为,"我们是彼此的制造者","我们可以集体学习如何像制造者那样行事"(19-20)。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视为 "代孕妈妈": 社会再生产理论是由一系列 "代用品"构成的:提供者、试验品、帮助和技术支持"(56)。
刘易斯要求我们承认代孕是一种工作,这也是增殖关爱关系的目标之一,正如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例如,Shalev Reference Shalev 1989;Humbyrd Reference Humbyrd 2009;Pande Reference Pande 2016;Rudrappa Reference Rudrappa 2018)。在此过程中,刘易斯将这一观点与那些认为代孕具有独特商品化特征的女权主义者区分开来(例如,帕特曼(Pateman),1988 年;拉丁(Radin),1988 年;安德森(Anderson),1990 年),或者认为代孕问题具体涉及性别(而非工作)不平等(例如,萨茨(Satz),1992 年),因此不应支付代孕费用。这一论点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家务劳动工资"(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相似,该运动呼吁将家务劳动归类为工作,也与当前性工作者寻求性工作合法化的运动相似。
在所有情况下,工人都可以让他们的劳动变得可见,他们可以组织工会、罢工,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他们还可以在替代性工作安排中组成集体(73、75、77、80)。刘易斯还主张工作中的 "无剥夺妊娠"(140)。这需要从堕胎到分娩的全方位权利,以及对妊娠相关疾病的更多研究。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妊娠者通过 "杀死 "胎儿进行罢工的权利(140),那么获得堕胎的权利尤为重要。刘易斯要求非妊娠者与妊娠者团结一致,以实现这一切(56)。在这些方面,问题不在于支持或反对代孕,而在于改善工作条件(44)。然而,作为工作的代孕只是 "最大限度地消除工作"(125)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需要先看到工作的存在(不一定是增加或享受工作),然后才能废除资本。
刘易斯的书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以及从事代孕、女权主义、家庭和反资本主义研究的人员都会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例如,在论述 "怀孕问题"(1)时,该书的分析令人钦佩地着眼于普通人。它吸引了所有怀孕的人,以及那些支持怀孕的人(即我们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从事小众代孕行为的人参与讨论。继舒拉米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之后,它将怀孕过程去浪漫化,显示胎儿寄生在妊娠者身上:怀孕是充满敌意和暴力的,而不是被动和无害的(费尔斯通参考资料,Firestone1970)。它揭示了任何妊娠过程中所涉及的巨大努力,这种努力是如何被归化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抵制这种归化,因为它使正在进行的工作变得无形。
刘易斯的建议也是激进而雄心勃勃的。它借鉴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批判,通过更多和更公平的商业代孕废除家庭的愿景是革命性的。它关注安妮塔-艾伦(Anita Allen)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论点,这些论点表明了美国黑人妇女在历史上是如何成为代孕妈妈的(没有技术干预),以及她们现在是如何继续被剥夺对其怀孕的充分支持或照顾的(艾伦参考资料-艾伦 1990 年;戴维斯参考资料-戴维斯和詹姆斯 1998 年)。该报告认为,资本促使我们将遗传婴儿视为私有财产--我们将所有婴儿个人化,从而将其商品化(116)--而这破坏了组织社会的更具公共性的方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该书包含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刘易斯认为代孕妈妈处于推动变革的最前沿,从而强调了她们的代理权和权力。一旦她们对更好的条件和集体的要求得到满足,刘易斯认为代孕妈妈很可能希望获得更广泛的生殖正义: "帮助过其他家庭的家庭可能会通过比报酬更有意义的团结形式建立持续的亲属关系"(147)。同样,刘易斯还利用了印度研究人员(如 Amrita Pande 和 Sharmila Rudrappa)的人种学研究,并引用了黑人女权主义者(如 Saidiya Hartman 和 Hortense Spillers)和机器人女权主义者(如 Donna Haraway)的研究成果。
刘易斯提出了丰富的分析和诱人的乌托邦,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问题仍然挥之不去;我在这里挑出三个这样的问题。
首先,这一愿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取的?
刘易斯正确地批评了那些想要取缔代孕的废奴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问代孕妈妈她们想要什么。刘易斯指出,各种研究表明,如果废除代孕妈妈去问,他们就会发现,全球的代孕妈妈实际上表达了对代孕交易、获得报酬和公平报酬的渴望。然而,据我所知,代孕妈妈也没有被问及书中所倡导的激进愿景--废除家庭--是否是他们想要的。这样看来,该书的核心论点似乎是在脱离代孕妈妈(实际上是所有怀孕者)的情况下提出的解决方案,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孕妈妈。提出一个普遍的、理想化的理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然而,鉴于当前废除代孕的辩论强调倾听代孕妈妈的意见,刘易斯显然不应该采用这种方法。
有证据表明,喀麦隆、菲律宾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有色人种已经在以 "多母性"(150)的方式抚养孩子,在这些社区中存在着多重和非正式的照顾。但是,正如刘易斯指出的那样,这种方式往往是出于需要,而不是人们想要的最佳方式。我不是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但也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想要。事实上,他们有理由不希望废除家庭。首先,被压迫民族可能希望保留"他们的"家庭,将其作为重要的反抗场所,正如刘易斯在谈到巴勒斯坦人寻求保留基因的体外受精时所指出的那样(155)。
其二,正如刘易斯通过戴维斯和艾伦(Allen Reference Allen 1990;Davis Reference Davis and James 1998)所论证的那样,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下,美国黑人在历史上一直被排斥在家庭之外,因此,这种制度可能是这些群体所希望融入的,而不是以平等为由予以废除。当然,这并没有削弱刘易斯的论点,但确实需要更多的辩护。
在考虑共同养育儿童的福祉时,也会对视野和方法产生类似的疑问。刘易斯提供了一项关于全球护理行业的研究,即全球南方国家的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庭去照顾全球发达国家的家庭,以此来证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根据一项研究(130),在菲律宾,这些家庭的孩子似乎并不介意这样的安排,他们大多过得很好,并与他人建立了亲密关系。刘易斯还提到了保护代孕妈妈遗传子女福祉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解释是爱而不是天性提供了家庭的稳定性,以及让孩子在家庭中经历更公平的分工(121-22)。
然而,这些仍然是在家庭结构的范围之内--例如,在菲律宾的案例中,有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家庭单位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完整的--这正是刘易斯所担心的安排类型。刘易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假设未来所有值得讨论的公社都是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地方。但这样做就有点把愿景中的家庭浪漫化了;刘易斯同时也想避免把怀孕或家庭浪漫化。同样,这并不是说这种安排没有积极意义,而是说它同样可能是消极的,研究本身并不能完全证明这种激进的设想是正确的。
其次,书中有多个目标,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显得有些矛盾或关系不明。举例来说,如果本书的目标仅仅是通过将代孕视为劳动并向妇女支付报酬,从而使代孕更加公平,那么这是一个项目。但是,如果这个愿景最终是反资本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就像刘易斯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支付报酬的想法,以及将围绕市场的规范附加到代孕上,似乎就成了不舒服的搭档。例如,商品化规范与市场相关,许多人认为这些规范会增加剥削、物化和异化的机会(例如,Anderson Reference Anderson 1990;Davis Reference Davis and James 1998),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目标的对立面。
此外,商业代孕是否是废除家庭的必要条件还不清楚。我们可以想象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共有家庭的愿景,尤其是刘易斯认为代孕工作是工具性的,是(与其他工作一起)需要消除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取消代孕来贬低遗传关系,因为代孕的出现是为了优先考虑和延续我们对遗传关系的推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开发替代代孕的更好、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这样就不会使现有的代孕妈妈处境更差。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对代孕工作的需求,又可以改善代孕工作者的就业机会,而且两者都不会破坏废除家庭的总体愿景。
如果刘易斯确实认为代孕对于实现愿景至关重要,那么他就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阐述。例如,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如何利用代孕来实现这一目标?是立即使用(因为妇女需要工作),还是在不久的将来使用(以修正后的形式使用,并做一些改进),还是在中期使用(只有在作为一个集体运行时使用,但仍在更广泛的资本主义背景下使用),还是在最终状态下使用(只有当每个人都在生殖公社中从事代孕工作时使用),还是以上都使用?每个阶段都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如果是立即,那么我们就继续以上述可怕的方式剥削代孕妈妈;如果是最终状态,那么我们就停止所有代孕行为,并在此之前取消代孕妈妈的工作选择。如果代孕确实是废除家庭的必要条件,而这又是呼吁我们为实现这些目标做些什么,那么进一步证明这种联系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可能会担心,在生殖公社中,谁会最终承担代孕的部分工作。刘易斯指出,并不是所有能够怀孕的人都会从事这项工作,就像并不是所有能够成为脑外科医生或垃圾收集者的人都会从事这项工作一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也适用于生殖公社。但是,在公社的愿景中,我们可能想要的另一种价值是,从事孕产工作的人的种类要公平。这样,有色人种妇女就不会像当前的资本主义环境中那样,既要承担过多的孕育工作,又不能提供自己的遗传物质(Banerjee Reference Banerjee 2014)。我们是否可以明确要求迄今为止拥有子宫的中产阶级白人承担起他们应尽的孕育责任,如果他们的贡献能得到体面的回报且具有社会价值的话?
刘易斯的这本著作极具煽动性,令人着迷,值得钦佩。这些评论都不是为了破坏以更加社区化的方式推广关爱关系的计划,而是对其具有建设性意义。这些意见也不只是刘易斯需要考虑或解决的问题。根据本书的精神,如果我们认为这一愿景值得追求,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Herjeet K. Marway 是伯明翰大学哲学系讲师。她的研究兴趣涵盖女权主义哲学、种族哲学和全球正义。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去激进化和关系自治、全球生物伦理(包括商业代孕)以及非疾病性状的基因选择。她是英国代孕组织的创始主席。
脚注
1。刘易斯可能会说,我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消除这类家庭,而是增加关爱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混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它如何与前面提到的科幻小说中的观点相吻合。当一些家庭可以选择坚守核心私人版本时,我们该如何认真地扩大关爱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细节可以在日后解决,但这里并没有暗示。
2.刘易斯可能会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工作都同样商品化,因此同样可行。但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既然我们最终要摧毁乌托邦中存在问题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在市场中支持有问题的工作(比如充满敌意和暴力的怀孕)呢?
出版信息
《现在全面代孕: 反对家庭的女权主义》(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索菲-刘易斯。伦敦: Verso, 2019 (ISBN: 978-1-78663-729-1)
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 2023 年 7 月 31 日
引用
- Allen,Anita L.1990.Surrogacy, slavery, and the ownership of life.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13(1):139-49.GoogleScholarPubMed
- Anderson,Elizabeth.1990.妇女的劳动是商品吗? 哲学与公共事务 19(1):71-92ScholarPubMed.
- Banerjee,Amrita.2014.种族与跨国生殖种姓制度:Race and a transnational reproductive caste system:Indian transnational surrogacy.Hypatia 29(1):113-28.CrossRefGoogleScholar
- Chodorow,Nancy.1978.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Berkeley:加州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Scholar
- Coontz,Stephanie.1992.The way we never were: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New York:Basic Books.Google Scholar
- Davis,Angela, Y. 1998.Surrogates and outcast mothers:九十年代的种族主义与生育政治》。In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ed. James, Joy.James,Joy.Malden, Mass.:Blackwell.GoogleScholar
- 恩格斯,弗雷德里克 1884/1972.《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纽约:Pathfinder Press.Google Scholar
- Firestone,Shulamith.1970.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伦敦:Verso.Google Scholar
- Haraway,Donna, J. 1991.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伦敦:Free Association Books.GoogleScholar
- Humbyrd,Casey.2009.Fair trade international surrogacy.发展中世界生物伦理学 9(3):111-18.CrossRefGoogleScholarPubMed.
- Mill,John Stuart.1869.The subjection of women.Indianapolis, Ind.: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8.CrossRefoogleScholar
- Okin,Susan.1989.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GoogleScholar
- Pande,Amrita.2016.《全球生殖不平等、新优生学与印度的商业代孕》。当前社会学专著 64(2):244-58.CrossRefGoogleScholar
- Pateman,Carole.1988.The sexual contract.The sexualcontract.
- Radin,Margaret Jane.1988.Market inalienability.Harvard Law Review 100:1849-1937.CrossRefGoogleScholar
- Rudrappa,Sharmila.2018.《印度禁止商业代孕为何对妇女不利?北卡罗来纳州国际法杂志》,43(4):70-95.Google Scholar
- Satz,Debra.1992.Women's reproductive labor.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1(2):107-31ScholarPubMed.
- Shalev,Carmel.1989.Birth power: The case for surrogacy.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Google Schola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