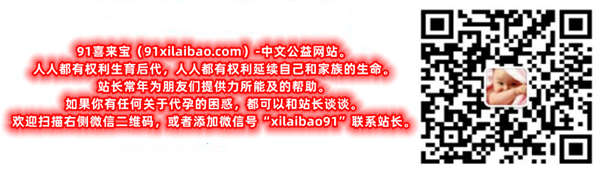提要:很多网友对于国内代孕充满疑虑,不知道现在国内代孕是否靠谱。站长找到一份关于当代中国代孕的学术论文,91喜来宝的网友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论文从宏观上了解当代中国代孕的情况。但需要留意的是:这篇文章成文于2021年,已经是四五年前了。而最近几年国内代孕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内代孕的风险类型跟以前也非常不一样了,站长希望网友谨慎。
建议阅读:中国代孕到底合不合法 国内代孕法律研究和建议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代孕的当前实践,并询问这些实践对人权意味着什么。妊娠代孕在20世纪下半叶首次在中国实施。政府对代孕的法律限制最少,导致地下代孕市场形成并扩大。本文将代孕的社会学视角与生物学数据和中国古代传说独特地结合起来。本文收集的数据来自其他关于代孕的学术文本,以及在线新闻媒体的详细数据收集。通过将代孕实践与人权联系起来,本文提供了多种视角,并比较了代孕与堕胎,将这些代孕实践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关键词:**代孕,中国,人权,女性主义
站长建议的相关阅读:
引言:
代孕是一种人工授精形式,其中精子和卵子被结合,而不是自然怀孕。代孕的概念被认为首先出现在圣经中,以解决不孕症问题。随后,由于传统代孕涉及大量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人类试管技术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妊娠代孕(Brinsden, 2003)。从哲学、道德和立法的角度来看,它比传统代孕具有更多优势。在以往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从法律、社会学或生物学的单一视角对代孕问题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分析,但缺乏有效的结合。基于此先前研究,本研究将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审视中国代孕问题,并将讨论其与人权的相关性。在中国,代孕是被禁止的,关于代孕的立法不完整(Ding, 2015),这导致了对代孕的一些误解。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上述问题:其对不孕个体、人类日常生活和政府决策的影响,以便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代孕。
本研究建立在先前探索中国代孕的研究基础上。Chunyuan Ding提出,中国最早的代孕起源于古代“男人想借用女人的肚子生孩子”的故事,因为人们希望通过代孕解决不孕症问题,并与他们的后代建立联系(2015)。E. Scott Sills和Peter R. Brinsden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代孕技术日益先进,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相继实施(2016)。但由于传统代孕涉及争议性的伦理问题,妊娠代孕应运而生。Chenzi Wei和Li Ji指出,尽管在中国代孕是被禁止的,但由于立法不完善,许多地下市场已经出现并难以打击(2019)。Tingting Yu和Chen Qin从正面角度讨论了代孕合法化的合法性,以及它能为整个社会和女性带来的好处。然而,他们也触及了学术界对代孕的批评(2020)。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并通过社会学、生物学和法律的视角分析其实践。在下一节中,我将提供中国代孕的历史及其发展。
中国代孕的历史及其发展:
代孕在过去一百年中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它对伦理和道德的挑战(Saxena, Mishra & Malik, 2012)。本文将探讨研究问题,中国代孕的当前实践是什么。为此,我将首先介绍代孕的历史,重点关注中国。根据基督教网站,"代孕"的概念最早在圣经时代提到,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代孕的历史",2020)。在撒拉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撒拉是不孕的,这打破了他们怀孕生子的梦想。因此,撒拉说服她的女仆夏甲成为亚伯拉罕孩子的母亲。幸运的是,夏甲为这对夫妇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以实玛利(Sills & Brinsden, 2016)。这是传统代孕的一个例子(也称为部分代孕),其中代孕母亲被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实际上,预定的母亲在生物学上与孩子没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孩子是“私生子”。遗传关系可能会在法律和情感上使传统代孕复杂化。由于这些复杂性,通常只有单身男性、同性男性夫妇或不能提供健康卵子的预定母亲会考虑这种方法。(Xiao, Li & Zhu, 2020)另一种主要类型的代孕是妊娠代孕(也称为完全代孕或IVF代孕)。1677年,显微镜的创始人列文虎克首次发现了人类精子。他还假设精子可以在女性的子宫中受精。1790年,苏格兰外科医生和性病学家约翰·亨特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进行了人工授精。他将自己的精子移植到妻子体内,妻子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1880年,人类首次尝试对兔子和豚鼠进行人工授精。十一年后,法国学者尼尔成功进行了人工授精并从兔子身上转移胚胎到另一个兔子身上。从1893年到1897年,V.S. Gruzdev得出了卵子对生育的重要性,并首次尝试在体外让兔子受精,这为体外受精铺平了道路。自20世纪以来,人工授精已成为处理不孕症的一种方法(Ombelet & Robays, 2015)。
自1980年代以来,妊娠代孕在中国得到实践。代孕的概念对中国来说并不完全陌生;“男人想借用女人的肚子生孩子”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因为人们希望与他们的后代建立联系。1988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北京成功分娩了第一批试管婴儿,1996年第一个代孕婴儿来到中国后,为了解决不孕症问题,对代孕的需求急剧增加(Ding, 2015)。此外,独生子女政策也导致对代孕的需求激增。在中国的贫困地区,人们更倾向于生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男孩可以为家庭做更多的工作,生女孩是“可耻的”的。有些人即使已经有六七个女孩,也会继续生男孩(“避免计划生育”,2020)。尽管偏爱男性,但一些父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去世后可以互相支持。然而,政府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干预使这些愿望变得不可能,因为限制了一对夫妇可以拥有的孩子数量。因此,许多人觉得他们唯一可以拥有更多孩子的方法是诉诸代孕。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务人员不得进行任何代孕程序。然而,这项法律并没有为执行代孕或捐赠者设定明确标准。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那些通过剥削经济上弱势的代孕母亲和迫切需要孩子的预定父母(包括代孕机构和个人)牟利的第三方几乎没有威慑力(Ding, 2015)。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对代孕“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从物理上反对代孕,因为它使传统道德和伦理复杂化,但仍有许多地下代孕市场在蓬勃发展(Zhang, 2020)。
深圳是中国地下代孕市场的一个例子。代孕来到深圳十年后,一个地下代孕市场逐渐出现。由于不孕症而产生的代孕服务为许多高收入的专业女性提供了生孩子的机会。总的来说,中国对代孕的监管仍在发展过程中。法律体系仍有许多改进以达到整个系统的成熟。
代孕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在代孕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Noel Keane,一位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律师,他将一生都致力于代孕,帮助许多不孕夫妇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Keane在1976年签订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代孕合同(Gelder, 1997)。尽管该合同在哲学、道德或法律上受到了批评,Noel仍然通过结合代孕母亲的卵子和生物学父亲的精子来支持代孕。
在一份典型的协议中,代孕母亲生下了一个有生物学父亲的孩子,然后将监护权交给了生物学母亲。从一些人的角度来看,生物学母亲只是孩子的收养者(Nakash & Herdiman, 2009)。
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的新泽西州。Mary Beth Whitehead以10,000美元的费用生下了William Stern的孩子。根据这份协议,Mary后来反悔,想要回孩子的监护权。最后,这件事上了法庭,William的妻子Elizabeth赢了。然而,州最高法院裁定代孕协议是非法的,所以Mary也保留了对孩子的探视权。Mrs. Whitehead起诉了Mr. Keane,称他没有充分筛选她。由于这个案子,许多州都有法律禁止人们从代孕母亲那里收养孩子。尽管如此,Noel还是保留了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不孕中心,并在七年后起草了他的第一份代孕父母合同。1983年,他推翻了收养制度,他说他已经联系了2000多对夫妇。他的不孕中心已经遍布全国: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纳、密歇根、纽约和内华达,他的行为给了没有孩子的夫妇希望。Noel Keane在代孕的发展中扮演了不可磨灭的角色。传统代孕方法虽然经过了很多讨论,但不可否认他在推动现代代孕方面的作用。(站长注:这就是著名的“Baby M案”)
中国代孕的当前实践:
中国代孕的监管困境 全球范围内,过去三十年来,代孕的接受度和实践都有所增加。然而,在中国,政府不支持代孕,导致地下代孕市场出现。抑制代孕变得越来越困难,对政府监管构成了巨大挑战。
- 首先,对非法代孕业务的行政处罚力度弱,代孕机构获得的利润高。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将被罚款不超过30,000人民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非医疗机构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人民币。由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制定得较早,非医疗机构的罚款金额远低于医疗机构。因此,非医疗机构比医疗机构更受欢迎。但风险在于它带来了质量较差的医疗安全。弱行政处罚不能完全抑制非法机构的发展,这意味着政府在中国实践的监管上存在空白。
- 其次,界定非法行为的界限很难。整个代孕过程包括精子和卵子的收集、胚胎的转化以及代孕母亲最终的分娩。然而,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它们将这些行为视为非法行为,但没有惩罚措施。换句话说,如果那些机构从事与医疗治疗无关的活动,政府没有权利或证据来监管它们。此外,一些机构会注册网站来推广代孕。根据国家安全部门的说法,他们只有权禁止赌博和色情。由于代孕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很难对涉案个人进行定罪。
- 第三,代孕立法不完整。如果国家卫生部门找到代孕母亲以调查非法机构,代孕母亲可以在那种情况下向他们撒谎或保持沉默。国家卫生部门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或测试代孕母亲是否说实话。此外,如果卵子、精子或两者都来自第三方,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魏和季,2019)。
代孕与中国女性(代孕妈妈):
由于中国传统信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男性是优越的性别。在就业、经济和教育方面,女性的地位居于劣势。即使现在,许多女性无法接受教育。相反,她们被期望成为家庭主妇,永远为丈夫服务并照顾孩子。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女性经济解放和独立时,女性的自信心和话语权才能增强(王,2019)。在中国,低收入女性特别是成为代孕母亲以实现经济独立。然而,中国关于代孕的法律不完整,代孕母亲和儿童的权益几乎得不到保护。下一节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代孕的实施,并提供一个背景来理解中国代孕的当前实践。
反对代孕:
当今世界有许多反对代孕的声音。例如,美国Creighton大学教授Charles J. Dougherty指出,代孕违背了传统观念:这是一种通奸行为,违反了自然法则。他认为代孕会导致乱伦,代孕母亲不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哈佛法学院的Martha Field教授还指出,代孕使成年子女感到羞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另一个母亲所生。此外,代孕扩大了贫富差距,让低收入女性出售子宫作为一种剥削形式。
家庭生活模式中的不平等:
家庭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为为什么低收入女性如此倾向于成为中国的代孕母亲提供了理解。由于女性的社会属性与男性不同:女性总是扮演生育的角色。由于女性的家务工作难以像男性赚钱那样被衡量,女性创造的价值容易被忽视。今天的女性通常被期望承受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压力,这也是女性生存的挑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3年,在有18岁以下孩子的工作父母中,母亲平均每周花费14.2小时做家务,而父亲为8.6小时。母亲每周花费10.7小时积极照顾孩子,而父亲为7.2小时。此外,由于男性在收入上具有绝对优势,他们也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在家庭方面,男性和女性很难完全平等。家庭生活模式的不平等导致许多女性的正常经济收入缺乏,这也是许多女性,特别是低收入女性选择代孕的原因。
代孕与人权:
许多人批评代孕,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美国学者D. Schuck认为,代孕母亲自愿签署代孕协议。生育后争取孩子的监护权并不意味着她们事先没有同意成为代孕母亲(Schuck, 1988)。国际上,生育权被视为人权。它不应由除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决定。事实上,生育权是生育自由。女性有权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决定生育的质量以及选择生育方式。堕胎政治和政策为理解代孕和人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堕胎法律同样展示了政府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她们的政治权利。2019年9月,阿拉巴马州通过了反堕胎法案,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堕胎。堕胎者被判处重罪谋杀,执行医生被判处99年监禁。这无疑剥夺了女性的自由选择权,给女性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阴影。“我大学时的男朋友在妈妈地下室强奸了我,‘不’这个词不在他的词汇表里。这永远改变了我。我从未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Jean R在推特上说。强奸是无法控制的,但强奸的后果是可以控制的。被迫怀孕的女孩有权选择生孩子,但她们也有权放弃,因为她们无法支持孩子。女性也是受害者。如果人权只关注未出生的孩子,那些女性的生活应该如何对待?现在许多女性受害者是看不见的,因为男性主导了世界。女性有时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受到歧视(Bunch, 1990)。她们受到政治压迫、性骚扰或家庭暴力。大多数时候,她们不愿意抵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应该剥夺她们的权利。
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代孕的历史、中国代孕的实践及其对女性的意义。在代孕历史的部分,我主要关注了中国代孕的兴起和全球范围。此外,我还提到了在代孕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军人物。在第二部分,我详细阐述了中国代孕的当前立法。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代孕对女性的影响,包括对代孕的批评、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以及对女性权益的探讨。本文建议,尽管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其高回报导致许多家庭和女性冒险。显然,代孕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需要对代孕实践进行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 Anonymous. Surrogate.com. The history of surrogacy. Retrieved Aug 11,2020, from https://surrogate.com/about-surr ... story-of-surrogacy/
- Anonymous. (2020, Aug 3) Avoiding family planning is the childhood memory of many rural children after 1990, SoHu News, Oct 25, 2020, from https://www.sohu.com/a/411355849 ... 00a.v1.0&spm=smpc.c srpage.news-list.35.1597461336981mvF1wrc
- Peter R. Brinsden. (2003). Gestational surrogacy. Oxford Academic. Volume 9, Issue 5, 485- 487. Retrieved from Oct 24, 2020, from https://academic.oup.com/humupd/article/9/5/483/727647?login=true
- Charlotte Bunch (1990). Women’s Rights as Human Rights: Toward a Re-vision of Human Rights. HeinOnline. Retrieved from Aug 27,2020, from https://heinonline.org/HOL/Landi ... q12&div=40&id=&page
- E. Scott Sills, Peter R. Brinsden. (2016). Handbook of Gestational Surrogacy: International Clinical and Policy Iss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unyan Ding. (2015). Surrogacy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Biosciences. (2) 33-34. Retrieved from Aug 11, 2020, from https://academic.oup.com/jlb/article/2/1/33/808655
- Lawrence van Gelder (Jan 28, 1997). Noel, 58, lawyer in surrogate mother cases, is dead.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Oct 26, 2020, from https://www.nytimes.com/1997/01/ ... rcases-is-dead.html
- A. Nakash & J. Herdiman. (2009). Surrogacy.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27(3). Retrieved from Oct 26, 2020,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 ... ?journalCode=ijog20
- Pikee Saxena, Archana Mishra, and Sonia Malik. (2012). Surrogacy: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d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Medicine. 37(4). 211-213. Retrieved from Oct 23, 2020,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31011/
- Peter H. Schuck. (1988). Some Reflections on Baby M Case. HeinOnline. Retrieved from Oct Aug 22, 2020, from https://heinonline.org/HOL/Landi ... 76&div=51&id=&page=
- W. Ombelet & J. Van Robays. (2015).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hurdles and milestones. Issues in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Retrieved from Aug 11, 2020,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98171/
- Qian Wang. (2019).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feminist socialis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men.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Retrieved from Oct 27, 2020, from http://www.cnki.net
- Chenzi Wei & Li Ji. (2019). Research on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supervision over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surrogacy. Soft science of Health, 33. 3940. Retrieved from Aug 25. 2020. From http://www.cnki.net
- Yongping Xiao, Jue Li, and Lei Zhu. (2020). Surrogacy in China: a dilemma between Public Policy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8-9. Retrieved from Aug 11, 2020, from https://academic.oup.com/lawfam/articleabstract/34/1/1/5864491
- Tingting Yu & Chen Qin. (2020).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legalization of surrogacy in China. Taiyuan University Newspaper.
- Zhouxiang Zhang. (Dec 9, 2020). Movie should have made clear surrogacy a crime. CHINA DAILY. Retrieved from Oct 25, 2020, from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 ... 1024ad0ba9aaab.html
翻译:
王前(2019年)。女性社会主义对当代女性发展的实践意义。法律系统与社会。检索日期:2020年10月27日,来自 http://www.cnki.net
魏辰子和李季(2019年)。辅助生殖技术与代孕监管的困境与对策研究。软科学与健康,33期,3940页。检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来自 http://www.cnki.net
肖永平、李爵和朱磊(2020年)。中国代孕:公共政策与儿童最佳利益之间的困境。国际法律、政策与家庭杂志。第8-9页。检索日期:2020年8月11日,来自 https://academic.oup.com/lawfam/articleabstract/34/1/1/5864491
于婷婷和秦琛(2020年)。中国代孕合法化的正当性。太原大学报。
张周相(2020年12月9日)。电影应该明确代孕是犯罪。中国日报。检索日期:2020年10月25日,来自https://www.chinadaily.com.cn/a/ ... 1024ad0ba9aaab.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