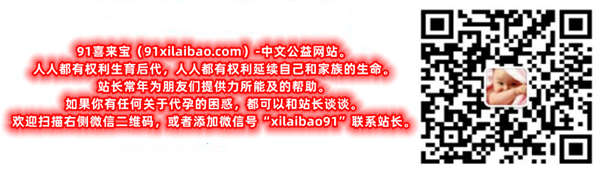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
提要:德国实体法中关于代孕和收养 根据《德国胚胎保护法》第7号第1(1)条和《收养安置法》第14b条,禁止商业代孕和利他代孕,这两项法律对从事代孕和促进代孕的商业活动(例如安置代孕母亲)进行处罚。但是,现实中德国并未对代孕母亲和预定的父母进行惩罚。这些规定的范围仅限于在德国境内实施的行为(《德国刑法》第7条)。
除了刑罚方面,《德国民法典》第1591条将生育的妇女定义为孩子的合法母亲,并排除了其他妇女的母亲身份,即使后者是孩子的遗传学意义上的亲生母亲。该条款尊重儿童与生母之间的社会和生物联系,旨在避免因代孕,包括在国外进行的代孕而导致的 "分裂 "母亲身份。联邦法院概述说,德国法律既没有规定承认父子关系的两人共同的法定亲子关系,也没有规定通过法律的实施将法定亲子关系分配给父母的登记伴侣;同性伴侣只能通过收养的方式建立共同的法定亲子关系。
德国联邦法院对于同性伴侣代孕亲权的观点 首先,将共同的法律亲子关系分配给同性伴侣本身并不违反德国联邦公共政策,因为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所谓 "连续收养 "的裁决--这种做法赋予一个人收养已经被其登记的伴侣收养的孩子的权利--已婚夫妇和以登记的伙伴关系生活的夫妇被认为同样适合提供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条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 2013年2月2日,案例1 BvL 1/11和1 BvR 3247/09,第80段,进一步参考=FamRZ 2013,521,527]。
德国弗莱堡阿尔伯特-卢德维希斯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y Freiburg )Dina Reis的报告
在2014年12月10日的裁决(案件XII ZB 463/13)中,德国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shof - BGH)必须决定,尽管德国国内禁止代孕,但是否应承认一项外国判决,该判决给予因代孕而出生的孩子的预期父母合法的亲权。
德国同志伴侣在美国加州代孕-案情概述本案的上诉人是一对居住在柏林的同性伴侣,他们是德国公民,并已登记同居伴侣关系一起生活。2010年8月,他们与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妇女签订了代孕合同。代孕母亲是美国公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在代孕过程中没有结婚。根据合同规定,利用1号上诉人的精子和匿名捐赠的卵子,通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怀孕。
在孩子出生前,经代孕妈妈同意,1号上诉人在德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获得承认了父子关系,并经加州普拉克郡高等法院判决,将合法的亲子关系完全指定给上诉人。2011年5月,代孕妈妈在加州分娩;此后,上诉人带着孩子回到德国柏林,并一直生活在那里。在民事登记处拒绝将上诉人登记为其子女的共同合法父母后,他们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下令民事登记处更改做法,但被德国下级法院驳回。
但德国联邦法院认为,不能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加利福尼亚州的判决,并命令民事登记处对孩子的出生进行登记,并将上诉人列为共同合法父母。联邦法院认为,在代孕亲权的案件中,如果预期父母其中一方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而代孕母亲与孩子没有任何遗传关系,那么如果仅仅是将合法的父母身份分配给预定的父母,并没有违反德国的公共政策。
'程序性'承认范围内的公共政策例外情况-德国代孕法律中亲权被承认首先,法院概述说,与单纯的登记或认证不同,加利福尼亚的判决可以得到德国《家庭事务程序和非诉讼管辖事项法》(FamFG)第108和109条规定的 "程序性 "承认,该条列举了拒绝承认的有限理由。
法院还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对代孕协议的有效性和由此产生的身份问题的实质性审查,而这是不需要审查的(即禁止 "重审")。根据第4号FamFG第109(1)条,如果一项判决导致的结果明显不符合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基本权利,将拒绝承认该判决(公共政策例外)。
法院指出,为了实现判决的国际承认,避免地位关系的换卵,对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况应作限制性解释。因此,仅仅是立法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违反国内公共政策;
德国国内法的基本价值与在本案中适用外国法律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必须是不可容忍的。
德国代孕亲权-父母一方的亲子关系关于1号上诉人的合法父母身份,法院指出,不能认定违反了公共政策,因为适用德国法律将产生与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裁决相同的结果。由于代孕母亲在孩子出生时没有结婚,而1号上诉人在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承认了父子关系,德国实体法(《德国民法典》第1592条第2款、第1594条第2款)也会将1号上诉人视为孩子的法定父亲。
将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分配给生父的登记伴侣并不违反公共政策。关于第2号上诉人的合法父母身份,法院认为,加利福尼亚的法院判决结果事实上偏离了德国国内对父母身份的认定。但是,如果预期父母之一与孩子有遗传关系,这种偏离就不会违反公共政策。
德国实体法中关于代孕和收养根据《德国胚胎保护法》第7号第1(1)条和《收养安置法》第14b条,禁止商业代孕和利他代孕,这两项法律对从事代孕和促进代孕的商业活动(例如安置代孕母亲)进行处罚。但是,现实中德国并未对代孕母亲和预定的父母进行惩罚。这些规定的范围仅限于在德国境内实施的行为(《德国刑法》第7条)。
除了刑罚方面,《德国民法典》第1591条将生育的妇女定义为孩子的合法母亲,并排除了其他妇女的母亲身份,即使后者是孩子的遗传学意义上的亲生母亲。该条款尊重儿童与生母之间的社会和生物联系,旨在避免因代孕,包括在国外进行的代孕而导致的 "分裂 "母亲身份。联邦法院概述说,德国法律既没有规定承认父子关系的两人共同的法定亲子关系,也没有规定通过法律的实施将法定亲子关系分配给父母的登记伴侣;同性伴侣只能通过收养的方式建立共同的法定亲子关系。
德国联邦法院对于同性伴侣代孕亲权的观点首先,将共同的法律亲子关系分配给同性伴侣本身并不违反德国联邦公共政策,因为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所谓 "连续收养 "的裁决--这种做法赋予一个人收养已经被其登记的伴侣收养的孩子的权利--已婚夫妇和以登记的伙伴关系生活的夫妇被认为同样适合提供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条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 2013年2月2日,案例1 BvL 1/11和1 BvR 3247/09,第80段,进一步参考=FamRZ 2013,521,527]。其次,法院指出,上述规定所依据的一般预防目标需要与在国外合法进行代孕的情况区分开来,因为现在必须考虑到儿童作为具有独立权利的法律主体的福利。但是,不能要求儿童对其受孕的情况负责。一方面,侵犯代孕母亲或儿童的基本权利可能意味着对公共政策的侵犯,但联邦法院强调,另一方面基本权利也可以作为承认外国判决的理由。
生母的人格尊严本身并不因代孕而受到侵犯:与收养相提并论关于代孕母亲,法院认为,仅仅是进行代孕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确定对人的尊严的侵犯。更何况,这适用于因代孕过程而导致出生的儿童。德国联邦法院强调,如果对代孕母亲是否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怀上孩子,并在孩子出生后将其交给预期父母产生怀疑,那么她的人格尊严就可能受到侵犯。
但是,法院认为,如果外国法院适用的法律规定了确保代孕母亲自愿参与的要求,并且代孕协议以及进行代孕的情况已经在符合法治标准的程序中得到审查,那么,在没有任何相反迹象的情况下,外国判决为代孕母亲的自愿参与提供了合理保证。根据代孕母亲在加州高等法院的声明,她不愿意对孩子承担父母责任。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代孕母亲生育后的情况与母亲将孩子送人收养的情况相当。
德国法律对于代孕的判决原则:注重孩子的最大利益
鉴于这些事实,法院得出结论,是否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决定应主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指导。为此,德国联邦法院提到了第2(1)条中规定的父母照顾的保障,以及第2(1)条中规定的对儿童的照顾。
第2(1)条与第6(2)条第一句规定的父母照顾的保障。《德国宪法》第6(2)条第一句规定了父母照顾的保障,该条赋予儿童被指定双亲的权利[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13年2月19日,案件1 BvL 1/11和1 BvR 3247/09,第44、73段=FamRZ 2013,521、523、526],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8(1)条的判例法。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的判例法,涉及尊重儿童私生活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后者包括儿童建立合法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权利,这种关系被视为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身份的一部分[欧洲人权法院2014年6月26日,第65192/11号----Mennesson诉法国,第96段]。
在此,德国联邦法院强调,代孕母亲不仅不愿意承担父母责任,而且事实上她也不能在法律上作为父母。将合法的母亲身份分配给代孕母亲,只有根据德国法律才能确定。但由于外国判决的反对,德国法律的规定在代孕母亲的母国没有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为,剥夺儿童与第二合法父母-子女关系,而第二父母与代孕母亲不同,愿意为儿童承担父母责任。所以反对把合法父母权利授予预期父母的做法侵犯了儿童在《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中规定的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第8(1)条规定的儿童权利受到侵犯。法院认为,代孕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身份关系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2(1)条和第8(1)条规定的要求。
2(1)条以及《德国宪法》第6(2)条规定的要求。《德国宪法》第6(2)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8(1)条规定的要求。欧洲人权公约》第8(1)条规定的要求。
德国联邦法院同意前一审的意见,即在本案中,视作收养是一种适当的做法。因为与根据外国立法机关对代孕案件的一般评估作出的判决不同,收养程序是对儿童最大利益的个别审查。然而,法院指出,在继子女收养案件中,这种个别评估的结果通常是有利的,因此与加州的判决相吻合,从而使生父或者生母的登记伴侣获得合法的父母身份。一致的判决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存在违反公共政策的问题。
此外,法院认为,收养不仅在儿童的出生国会遇到实际困难,因为上诉人已经被认为是合法父母,而且还会给儿童权利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如果孩子出生时有残疾,则由打算收养孩子的父母自行决定是承担父母责任还是改变主意不收养孩子。
结论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在德国学术界和法律实践中得到了认可[见Helms的说明,FamRZ 2015,245;Heiderhoff NJW 2015,485;Mayer,StAZ 2015,33;Schwonberg,FamRB 2/2015,55;Zwißler,NZFam 2015,118]。在该判决之前,下级法院已经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认为仅仅是进行了代孕这一事实就违反了公共政策[参见柏林高等地方法院2013年8月1日,案件1 W 413/12,第26段及以下=IPRax 2014,72,74及以下;柏林行政法院2012年9月5日,案件23 L 283.12,第10段及以下=IPRax 2014,80及以下]。
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对公共政策例外的处理更加谨慎和有条不紊[特别参见Heiderhoff,NJW 2014,2673,2674和Dethloff,JZ 2014,922,926等,并附有更多参考文献]。BGH的裁决没有诉诸于对整个代孕的否定,而是基本上建立在对现有具体替代方案的准确分析和对本案可能结果的批判性评价之上。
然而,有人指出,在代孕这一复杂的领域中,本案的情况过于简单。例如,代孕母亲没有结婚,因此生父可以在没有复杂情况下承认父子关系;预期父母和代孕母亲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后者不想留下孩子。而且预期父母的合法父母身份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程序中确定;孩子和代孕母亲的权利,特别是她的自愿参与代孕,并已经受到审查[参见Heiderhoff, NJW 2015, 485]。
德国联邦法院明确表示,如果预期父母双方都不是孩子遗传学意义上的亲生父母,或者如果代孕母亲也是遗传母亲,那么不同的结论是否合适,尚无定论[第53段]。
法院也没有讨论 "承认"公民身份情况和文件的问题。
此外,在人权标准较差和对司法信任度较低的国家进行的代孕安排,可能不符合《欧洲人权法案》规定的承认要求。
就目前而言,该判决可能会对在不符合所需标准的国家寻求代孕产生威慑作用[Heiderhoff,NJW 2015,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