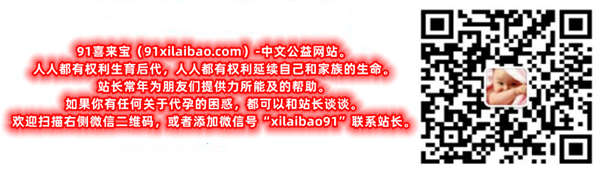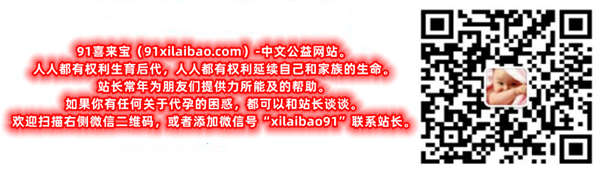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
前几日有一位香港网友通过微信问站长关于“香港居民在国外合法代孕后,孩子回到香港会面临无法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问题。为此站长把香港居民在国外代孕后,孩子在香港的身份和权利问题的严肃法律文章贴到这里,希望能帮到香港的朋友。 本文中,香港居民在国外代孕后,香港政府不承认在国外合法代孕的孩子的香港合法身份,但业内人士说如果有“ 海牙认证”可以规避这个问题。站长认为通过在内地代孕也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因为内地的代孕行业实务操作中, 代孕妈妈会用女性雇主的身份文件建档,做孕检、入院分娩,宝宝的出生证明关于“母亲”那一栏里写的也是女性雇主的名字。所以回到香港后,只要你不主动告诉香港政府或者法院宝宝是代孕出生的,就不会有人知道。 最近,香港高等法院的两宗案件可能为放宽香港对代孕的立法限制以及潜在的正式法律检讨和改革打开了大门。我在2018年发表的两篇文章Lexis Nexis International Family Law Journal的文章" Avoiding the cross hairs - crimin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surrogacy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UK "([2018]1FL95),以及2018年5月在《香港律师》发表的文章《香港的代孕法所面对的复杂情况》:http:这两宗案件均由欧阳桂如法官主审: FH v WB[2019]HKCFI 1748(FH)-判决日期为2019年7月15日;以及A&B(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第429 章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2019]HKCFI 1749(A案)-判决日期为2019年10月14日。
以上是首两宗充分承认和处理有关第17条刑事责任问题的个案。正如我的文章所解释,截至该等文章发报之日,香港仅有的两宗被报导之代孕个案(D(「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Parental Order")[2014]HKEC 1948及S v J(代母:监护)[2017]HKEC 1998)并没有承认和处理这刑事责任问题。此外,《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施加的刑事责任与第429章《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下的批准费用条文之间的冲突,(在当时)仍然是一个被误解的陷阱。这就是我所说的「获批准费用陷阱」:在FH案,法官第一次承认《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和《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在这方面的「冲突」。
在FH案中,FH和MH(「拟作为父母的人」)是已婚的美国公民和香港永久居民。他们被介绍给加州的一家代孕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再把他们转介给WB和HB这对已婚夫妇。FH和MH与WB签订了一份「妊娠承载者」协议,由WB作为「妊娠承载者」。
加州法院裁定,申请者是这对双胞胎的亲生父母和合法父母,而WB和她的丈夫HB并不是这对双胞胎的合法父母。在加州签发的双胞胎出生证明文件上,申请者被记录为双胞胎的父母。
2018年1月中旬,FH为这对双胞胎的受养人签证申请续签。FH透过律师回答入境处处长(处长)的问题时,曾向处长透露该对双胞胎是由代母安排所生,并打算提出申请「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
这对「拟作为父母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需要香港的「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虽然听取了加州的法律建议,但法庭在其判决指,「FH在2018年2月20日收到处长的一封信,要求他提供产前检查文件与MH的双胞胎怀孕期间的怀孕照片,以及在双胞胎出生当天和之后不同时期拍摄的五张家庭照片,FH才意识到申请「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需要。」
FH随后咨询了香港的法律意见,发现加州法院的判决不被香港法庭承认。根据香港法律,无论加州法院的立场如何,他们都需要取得「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FH还被告知,如果不首先根据香港法律确定这对双胞胎的亲子关系,便很难为他们申请独立签证。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受养人签证或「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这对双胞胎就不能注册入读香港的幼稚园。
法庭还指出不颁发「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其他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被忽视),并强调取得「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能加强代孕出生的子女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机会。法庭在判决中引用了英国A v P[2012]Fam 188一案。在该案中,法庭描述了不获发出「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后果:
- 子女和他的生父(也是委托父亲)之间没有法律关系。
- 子女被剥夺了这种关系受到承认所带来的社会和情感利益。
- 如果子女在法律上不被承认为他父亲的子女,(就继承方面而言)他/她可能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 子女不能得到跟日常现实互相匹配的法律现实。
- 子女因生父去世而进一步被处于不利地位。
香港法庭裁定:「如果子女只获发访港签证或受养人签证,而委托的父母则拥有香港居留权,这并不符合该子女的最佳利益。「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作用是加强子女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机会。」
FH先生和MH夫人需克服两个重要的障碍:
- 他们申请「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时已超过了6个月的限制;
- 以及他们显然是无意中犯下了违反《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的刑事罪行。
对于这两个障碍,法庭找到了一个务实的解决办法。
《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2)条规定的6个月期限
为了取得「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2)条规定已婚的「拟作为父母的人」必须「在子女出生后6个月内」申请「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而本案有关的「拟作为父母的人」却在6个月的限制期之后才提交申请。
法庭认为,《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2)条中的6个月期限「并不含糊」,但严格遵守这一规条可能会导致「荒谬」的情况:「一个儿童可以有两对合法的父母⋯⋯该儿童将没有身份⋯⋯同时,代孕母亲可能在她生育的司法管辖区内已经放弃其对有关子女之父母权利,或者(如本案一样)从未享有对该儿童之父母权利。」
法庭认为,「鉴于「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重要性,立法机构不可能有意将这样的后果强加给那些没有选择用这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而儿童的福利是法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考虑到福利原则和法律解释的原则后,法庭了引用了英国Re X(A Child)的案例来裁定自己有权延长时间限制,并指出儿童的福利胜过他/她的父母在提交申请方面的拖延。
法庭再透过其他两条香港法规来解释第12(2)条,以进一步证明其对延长提交申请期限之权力:
- 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4(1)条,保障私生活和家庭;
-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9(1)条,保障家庭权利;
-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0条,保护儿童在出生方面不受歧视的权利;以及
- 《基本法》第35条,保障诉诸法庭的权利。
- 《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下的刑事责任及「获批准费用陷阱」
《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39条将违反《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的行为定为刑事罪行,首次定罪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及监禁6个月。根据第227章《裁判官条例》第26条,这是一项简易程序罪行,检控时限为「申诉或告发须分别于其所涉事项发生后起计」的6个月内。
就法庭表示其「主动引用了《人类生殖科技条例》,以确定代孕安排相关的款项是否违法,并考虑应否将申请人转交律政司检控」,这对「拟作为父母的人」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可能触犯了《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的刑事罪行。正如我在《香港律师》文章中强调,英国法律并没有同等的条例可将「拟作为父母的人」定罪。
法庭虽裁定FH和MH已触犯罪行,但检控已超出时限:「根据第227章《裁判官条例》第26条,这是一项简易程序罪行,『由该投诉或告发分别发生之时起计』,时限为六个月,时限内可作检控。而且,「拟作为父母的人」「参加了谈判,以期达成「妊娠承载者」协议。他们分别在-2014年12月24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10月27日和2015年12月10日支付了四次款项。检控显然已超出时限。」
法庭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获批准费用陷阱」的情况是「《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和《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1)条之间的冲突」:
「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7)条,这里亦涉及代孕安排所衍生的部分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具体来说,其中一些费用可能违反了《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和/或39条。虽然可对申请人提出检控的六个月期限已经届满,但是否应以符合申请人宪法权利的方式解读出《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和第39条,则仍有存在问题。」
「这是法庭第一个必须评估费用合理性的代孕案例。如果儿童的父母对法律一无所知,而且在香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案例让他们了解法庭的观点,而导致儿童「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被剥夺是不公平的……鉴于《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7)条与《人类生殖科技条例》17(1)条之间的冲突……,法庭一方面需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7)条(通过出非合理费用测试)批准费用,但同时根据《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1)条及第2条,任何有关代孕安排所衍生之费用均被视为违法。在此,法庭被处于相当尴尬的立场。」
法庭拒绝重新解释/解读《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和第39条。法庭裁定,由于检控已超出时限,故毋须提出检控,并在严格审查逐项已支付的费用后,批准合共108,198美元(约港币840,000元)的所有费用。
当然,法庭在作出最后裁定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该案的若干关键因素,包括FH及MH并无企图欺骗当局(包括处长)。
法庭承认,「第12(7)条在英国的对应者是1985年《代孕安排法》(Surrogacy Arrangements Act)第2(1)条的前身。该条文禁止了商业代孕,但没有《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的域外效力。」即使代孕母亲和「拟作为父母的人」在英国收取或支付代孕相关款项(而该等款项在香港是违反了《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但判决书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在英国犯罪。可是,在英国,由中间人支付或向中间人支付相关款项则是违法。这就是英国在案例中没有讨论「拟作为父母的人」是否触犯了刑事罪行的原因。
法官指出:「《人类生殖科技条例》针对的是担心代孕安排会被商业化及其被滥用的情况。 因此法例要同时惩罚付款人和受款人。立法机关的用意并不是要阻止像申请人这样真正需要依赖代孕安排并使用自己的精子和卵子的已婚夫妇。」
因此,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拟作为父母的人」犯了违反《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的罪行,但他们的罪行尚未超过被检控期限的话应怎样处理。法官表示,「任何有关解读 《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的问题,应留待日后更适当的案件处理。」尽管如此,她已明确指出,《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与《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2条及第17条需进行检讨(见下文)。
A案中的情况跟FH一案有相似地方,但A案是与中国大陆有关连。A案重申了上述大部分的法律原则。申请人是一对已婚夫妇,自2008年以来一直同住在香港。他们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他们通过中国大陆的代孕机构达成代孕安排,由E在一家医院担任代孕母亲,使用一位匿名女性捐赠者的卵子和A的精子进行。申请人获得E的同意,提出了「获判定为父母的命令」的申请。跟FH的案件一样,申请人逾期提出申请,申请人亦有违反《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的问题。同样地,法庭发出指令,指检控已超出时限,然后经过彻底审查后,把所有代孕安排有关之费用批准。
FH案是主要判决而A案判决与FH案相互参照,反之亦然。
代孕法检讨和改革的迫切需要
自2002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对代孕法进行国际监管/改革:
我在W v H (子女)(代孕:惯常居所)[2002]1 FLR 1008和W v H(子女)(代孕:惯常居所)(No 2)[2002]2 FLR 252,一宗被报导的加州/英国案中为英国代孕母亲H于伦敦高等法院及上诉法院的代表律师。此案被判决后,我于2002年在伦敦《律师会公报》上呼吁对英国和加州之间的国际代孕法进行规管。
我于2015年6月18日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称,「现在是时候进行国际代孕法监管了」而且「全球代孕法律的复杂程度埋伏了很多陷阱,正等待法庭来收拾残局……法庭亦需要向所有正在考虑进行国际代孕安排的人发出明确的警告:在进行任何代母安排及怀孕之前,应及早于所有相关司法管辖区寻求专家法律意见,并考虑所提及之陷阱问题。」
我在《香港律师》的文章中呼吁香港进行代孕法律改革。在文章中我亦明确指出,香港的代孕法律在某些方面具有歧视性,并指出了贩卖儿童的忧虑。
自此之后,我们终于首次收到香港司法机构赞同检讨/改革代孕法例的讯息。
在FH案中,欧阳桂如法官引用Re L(Commercial Surrogacy)[2010]EWHC 3146(Fam),§10表示,「《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与《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2条及第17条均须予检讨」:「如要管制商业代孕安排,该等管制须在法庭程式开始前(即在边境或什至之前)实施。如立法机关有此意图,管制应在订立代孕安排前实施,这便是最好的做法。」她还表示,「于2018年5月,英国政府已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检讨有关代孕的法律。」从这些评论和法官两案判决的主旨可以合理推断,法官可能在表示对委员会关于「代孕途径」「成为合法父母的新途径」的初步建议有一定的支持。这些成为合法父母的新途径涉及受孕前协议和「拟作为父母的人」从出生起的合法父母关系。
法官Zervos JJA在HKSAR v Yeung Ho Nam[2019]HKCA 384上诉一案中处理了歧视性和违宪的香港立法问题。法官Zervos JJA表示:
「3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社会团结的一个基本核心原则。从这项核心原则引申出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不应因为性别或性取向等原因而受到歧视。」
「49.歧视同性关系的法律和政策需进行适当和有效的检讨,而不应让法庭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序来解决这问题⋯⋯」
「50.法庭曾在法例于宪法上之有效性存在清楚和明显问题的情况下让当事人对该项法例提出诉求。这一点在 Le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一案中可见⋯⋯法庭当时指出,如果一项法例违宪,越早发现越好,强迫有关人士采取「观望态度」然后才处理事情是不可取或有伤害性的。法庭亦注意到,香港法庭有责任执行和解释《基本法》。因此,如果有任何法例违反《基本法》(或《人权法》),该法例必须被裁定为
无效。」
《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把参与商业代孕安排(不仅是对进行商业交易者,甚至「拟作为父母的人」亦然)定为刑事罪,已经鼓吹及继续鼓吹代孕安排在秘密中进行。这造成了一种情况,即通过这种安排出生的子女会被剥夺法律最基本的保障,包括法庭命令授予一个或多个「拟作为父母的人」的父母所在地
(parental locus)。
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第12条,所有同性伴侣均不得使用代孕服务。这可说是与下列宪法权利极不相容:《基本法》第25条订明,所有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2条订明:「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应受法律平等保护,无所歧视。」
就挑战《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第17条而言,法庭亦认为直接受第17条影响的人会挺身而出的可能不大,因为接受挑战这项构建罪行的条文的做法基本上是意味着要冒刑事检控的风险。基于这种情况下,对于「拟作为父母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符合Zervos JJ所述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强迫他们这样做是「不可取或有伤害性的」。这些案件很可能是那些「不应让法庭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式来解决」的案件。
请恕我直言,如果律政司司长决定回应司法界这项强大而急切的呼吁,对香港代母法例进行检讨,并在处理或寻求解决任何歧视性和违宪法例的问题时避免昂贵的法庭诉讼的话,考虑按照委员会最初的建议,则实施香港「代孕途径」(包括怀孕前协议和「拟作为父母的人」从出生起的合法父母关系),可能是一个适合的起点。同时,对于异性和同性伴侣亦应作出相应的措施。
关于本文原作者:Marcus Dearle
国际律师协会家事法律委员会高级副主席及国际家事法律师学会(IAFL)成员
Marcus Dearle 是国际律师协会家事法律委员会高级副主席及国际家事法律师学会(IAFL)成员。他是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 合伙人及其设在香港及伦敦的家事法团队之全球负责人,更是香港主要的家事法、信托和离婚律师之一。他带领的团队在香港参与了很多举足轻重的案件,包括在 TCWF v LKKS [2014] HKEC 1593 一案代表案中之妻子、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终审法院信托及离婚案 Otto Poon一案代表案中之受托人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以及在 LCYP v JEK 一案代表案中之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