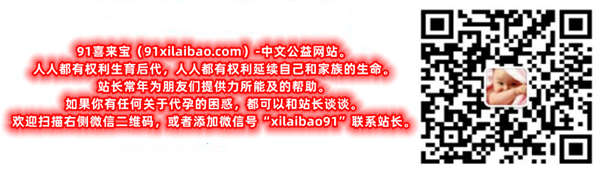根据赋予妇女权力和父母权利的呼吁,现在是时候让马来西亚踏上医疗行业的新天地,使马来西亚商业代孕合法化。只要有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的指导,并向那些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学习,代孕会对预期父母和代孕妈妈都得到好处。
一.本文概要
怀孕和生育被认为是人类最敏感和神圣的事情。因此,有些人认为租借子宫(代孕)的做法是亵渎神明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妇女自愿让自己的身体承受怀孕的压力,只是为了把孩子交给其他人,这当然是荒谬的。话说回来,这正是商业代孕,而且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商业代孕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巨无霸。2016年以前,仅在印度就有近百亿美元的收入。[1]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商业代孕已被一些国家禁止,如英国、加拿大,甚至在印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商业代孕有什么不好的方面?毕竟,商业代孕对不孕夫妇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同时为愿意成为代孕妈妈的妇女提供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因此,本文的目的有两个:
- 第一,表明那些禁止商业代孕的国家只是无法对其进行监管;
- 第二,商业代孕在有效的法律框架下,可以对不孕夫妇和代孕妈妈都有好处。
A. 马来西亚代孕的情况
在马来西亚,没有具体的法律来规范代孕安排。因此,在代孕安排的合法性方面,存在着法律上的空白。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医学委员会已经声明,代孕是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主要宗教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可能会导致有关个人的许多法律困境。
B. 本文讨论的范围
本文的范围是解决与商业代孕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申明这样的立场:代孕行业在适当的监管下是有益的。然而,本文只关注马来西亚国内环境下的商业代孕,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代孕。因此,不涉及不同国家的代孕问题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二、不同类型的代孕安排
A. 妊娠代孕
一般来说,代孕意味着一名妇女同意怀孕,并为"预期父母"(或称作"委托父母")孕育和分娩一个孩子。妊娠代孕安排涉及通过试管婴儿人工生殖技术(ART)使代孕妈妈受孕[3],而代孕妈妈与她所生的婴儿没有遗传上的关系。现代各国的代孕,大多数代孕安排是妊娠代孕。在妊娠代孕中,预期父母都可能是婴儿的遗传父母。因为如果预期母亲使用她自己的卵子和预期父亲的精子,则预期父母都是代孕出生的孩子的遗传学亲生父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使用捐赠者的精子或者卵子[4]。
B. 传统代孕
在传统代孕(有的地区也被称为“遗传代孕”)中,采用体外人工授精(IVF)的方式,让预期父亲的精子和代孕妈妈的卵子结合授精。在传统代孕的情况下,婴儿在生物学上与代孕妈妈和准父亲有遗传关系。诚然,这是简单省事省钱的代孕形式,但它需要付出更沉重的情感代价。代孕妈妈必须交出她的亲生孩子,而预期母亲则必须接受她丈夫与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孩子。
C. 利他代孕
利他代孕是指代孕妈妈只得到与怀孕和孩子出生相关且必要的费用报销,而不是代孕服务本身。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妊娠代孕安排,都可能是“利他代孕”。它经常发生在亲戚或亲密的朋友之间。[6]从本质上讲,利他代孕就像去掉一些法律争议的商业代孕,因为不具备商业代孕中存在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然而,从各国利他代孕实践看,可以说仅靠利他主义代孕无法满足对代孕服务的需求,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在没有足够补偿的情况下为他人生下孩子,即使是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所以利他代孕基本无法解决问题。
D. 商业代孕
商业代孕是指代孕妈妈因生育预期父母的孩子而获得经济补偿。商业代孕合同与其他商业协议一样,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但敏感和微妙的代孕为合同的法律,为商业代孕合同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商业合同的争议。
三、支持马来西亚商业代孕合法化的论点
A. 赋予代孕妈妈权利
商业代孕不仅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产业,而且还为妇女平权铺平了道路。马来西亚在1995年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9]在第3条中指出,"确保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以保证她们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提高妇女地位应包括进行商业代孕的权利。
代孕妈妈相关的研究表明,她们常常对代孕工作感到满意和自豪,并能够自我认同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尽管在与预期父母的联系减少时有失落感。[10]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代孕是代孕妈妈做出的决定,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主张身体主权并表达自由意志。因此,禁止代孕可以说是对妇女赋权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妇女不能对她们认为对自己的身体有益的事情行使自由意志。
此外,为了与美国最高法院对Johnson诉Calvert一案的判决产生共鸣,妇女在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自愿为预期父母孕育分娩婴儿的结论,给持续了几个世纪的阻止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和职业地位的厌恶女性的观点带来了变化。美国最高法院强调,"禁止女性自愿为他人代孕的观点既是排除了代孕妈妈的人身自由和经济选择,也是剥夺了预期父母生育孩子的权利”。
1. 经济选择中的自主权
每个人都有不可否认的个人自主权,对自主权的尊重意味着对生育自主权的尊重。[12]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第12条,签署国必须保障健康权,其中包括性和生殖自由权,以及决定对自己进行医疗的自由。 [13] 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和第7条规定的工作权利结合起来,这包括自由选择作为代孕妈妈的权利。此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7条规定了隐私权,[14]这被解释为包括生殖自主权。[15]因此,在马来西亚不允许商业代孕,阻碍妇女权利和上述公约的进步,特别是马来西亚批准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
2. 生儿育女为人父母的权利
有些人梦想拥有完美的事业,统治世界或在扑克游戏中获得满堂彩。许多人把为人父母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充实和满足的梦想。相关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有孩子的父母比没有孩子的人更幸福。[16]虽然生孩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有困难,但在Kealey诉Berezowsk一案中,抚养孩子的责任被描述为 "成功地履行父母养育孩子的责任也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即个人满足和幸福。 '[17]然而,即使是马来西亚医学委员会也承认,有些人并不幸运,因为他们无法怀孕。这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个人痛苦和家庭生活的破坏,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同样的影响。
许多人被剥夺了 "育儿权 "或 "生殖权",因为这项权利可能还没有被编入任何国际协定或人权公约。然而,《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6.1条[19]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3条规定,"成年男性和女性有权结婚和组建家庭",对于这一点,它指的是父母身份。[20]然而,这一条款并没有明确说明它是否禁止通过收养或代孕成为父母。在二十一世纪,组建家庭的形成和方式给人权的界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 "家庭 "一词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世界人权宣言》确实指出,包括获得特殊照顾和帮助儿童的权利,[21]母亲的权利也应受到保护。[22]因此,对组建家庭的方式没有明确的限制。
因此,商业代孕所做的是为不孕不育的夫妇提供新的生儿育女的机会,以行使他们为人父母和组建家庭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获得新形式的幸福和个人满足。有人可能会怀疑代孕的必要性,并提出收养已经是解决不孕不育的充分办法。然而,"代孕程序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作为收养的替代方案,规避了等待健康婴儿的漫长时间。"[23]此外,对准父母来说,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通过代孕生儿育女,他们将要抚养的婴儿与自己有遗传联系。 毕竟,血浓于水,确保自己的血脉传承可被视为任何生物中最原始的本能。因此,很明显为人父母的权利应该扩展到商业代孕,作为追求幸福的一部分和建立家庭的一种手段。
世界各国代孕研究和比较
1. 对父母权的限制:对英国的案例研究
英国是一个禁止商业代孕但允许利他代孕的国家。这导致了一个糟糕的代孕立法模式。为了理解代孕目前在英国的法律地位,必须研究法律的历史沿革。这一切都始于英国第一个商业性的代孕婴儿--Baby Cotton。[25] 这个案例涉及三个国家。瑞典、美国和英国。在这个案例中,英国公民Kim Cotton得到了6500英镑的报酬,在英国的一家试管婴儿诊所的帮助下,为居住在美国的一对瑞典籍夫妇生下了一个婴儿。英国当地政府进行了干预,将该婴儿作为"安全场所"命令的对象,并调查了预期父母的背景和信用。[27] 最终,瑞典预期父母获得了婴儿的监护权,并将她带回了美国,因为这是孩子的最佳利益。[28]"婴儿换现金交易 "在英国公众中引起了争议,导致全英国禁止商业代孕安排。
英国为什么禁止商业代孕?这是由于剥削以及贩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30]沃诺克委员会强调,"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剥削的危险,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远远超过了潜在的好处。"[31] 委员会还得出结论,仅仅为了方便而代孕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32],并建议将商业代孕定为犯罪。
因此,英国《1985年代孕安排法》(SAA 1985)得以颁布。[34]其规定是基于1984年人类受精和胚胎学调查委员会的建议。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像Childlesness Overcome Through Surrogacy (COTS)、Surrogacy UK和Brilliant Beginnings这样有信誉的代孕组织必须在非盈利的基础上运作,这些组织协助预期父母和代孕妈妈相互联系。 [37]此外,宣传愿意参与或促进代孕也是一种违法行为。[38]因此,其效果是,如果一对夫妇希望通过代孕生子,他们必须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私下寻找自己的代孕妈妈。
然而,1985年的法案被批评为考虑不周,而且基本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措施,因为政府在公众不满后匆忙通过了该法律。 [40]此外,英国1985年的代孕监管法案和沃诺克报告都对孩子的福利问题没有清晰的表述,也没有制订相关标准。 [41]在1985年SAA颁布五年后,1990年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解决了通过辅助生殖方法怀上的孩子的合法父母身份问题。[42]该法规引入了父母令(Parentage Order),使合法父母身份从代孕妈妈(还有她的丈夫-如果有的话)转移到预期父母身上。
然后,1985年的SAA被修订为1990年的SAA。2008年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案》(HFEA 2008)对1990年的法案进行了修改,将关于合法父母身份的规定扩大到那些通过辅助受孕建立家庭的人。[44] 在英格兰,代孕妈妈保持对孩子的合法权利,因为她被认为是合法母亲,即使他们在遗传上没有关系。这是2008年HFEA第33条和1981年《英国国籍法》第50(9)条的规定。如果代孕妈妈已经结婚,合法父母就是代孕妈妈和她的丈夫,因此,作为亲生父母的任何一方都与孩子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为了使情况恶化,1990年的法案插入了一个新的条款,即S.1A,使代孕合同不被承认,更无法强制执行。[46] 预期父母的唯一途径是向英国法院申请孩子的亲权令,法院将根据孩子的最佳利益来决定。[47]英国代孕相关法律很难保护预期父母的亲权,因为英国代孕法律严重偏袒代孕妈妈。例如,代孕妈妈是合法母亲,除非预期父母有法院给出的父母令(Parentage Order),而且代孕妈妈可以拒绝归还孩子。[48]这可能会使预期父母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代孕妈妈。
因此,英国不允许代孕安排中对代孕妈妈进行补偿,只能报销必要且合理的费用。英国《代孕安排法》概述了在英国进行代孕的严格标准。这些限制导致英国的预期父母们不得不到国外寻求商业性的代孕服务。[49]这表明,英国关于代孕的法律框架极大地阻碍了人民的生育权,但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代孕的需求,导致了到其他国家的医疗旅游。
从中吸取教训,马来西亚最好为商业代孕形成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剥夺其公民的生育权。
2. 马来西亚商业代孕合法化的障碍
尽管商业代孕有许多好处,但商业代孕合法化必须谨慎行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障碍需要解决。然而,本文将不会讨论有关商业代孕的每一个问题。然而,我们将讨论与商业代孕最相关的马来西亚国内法律和伦理问题。
A. 对代孕妈妈的剥削
现在,看看商业代孕获得各种好处的另一面,必须解决商业代孕中对代孕妈妈的剥削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有必要照顾代孕妈妈的权利,因为她们是商业代孕安排中"经济上和情感上最脆弱的一方"。[50]剥削不一定是法律禁止一项交易的理由,但如果这项交易造成伤害或不合理的风险,这项交易可能被禁止。如果代孕给这些弱势妇女带来了伤害,包括她们的生命安全、健康和自由。这是因为剥削源于缺乏知情同意。有人认为,在这个商业代孕生殖行业中担任代孕妈妈的妇女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的权利缺乏适当的了解。虽然没有确凿的研究证据表明妇女不了解代孕的风险,但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必须仔细评估,因为对贫困妇女的能力做出这样的负面假设是合乎现实的。
在商业代孕行业,代孕妈妈的意愿可能会因为经济窘迫程度的影响,因为最贫穷和脆弱的妇女最容易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与利他主义的代孕协议大相径庭,后者没有经济激励。[53]显然,在乌克兰,代孕妈妈的收入是平均年收入的八倍。[54]这为这些妇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赚钱机会。然而,报告显示,有的代孕妈妈受到虐待。如果她们流产,甚至不会得到补偿。[55]这些妇女通常被自己的代孕合同所困,不知道自己的风险和权利。此外,在印度或泰国这样的国家,对代孕妈妈来说,安全和有足够报酬的工作选择有限。[56] 因此,经济压力导致妇女在商业代孕中可能受到剥削。[57]
1. 未受教育、未受保护和易受伤害。关于印度的案例研究
2002年,印度将所有类型的代孕合法化,包括商业代孕,直到2015年11月商业代孕在印度被禁止。[58] 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有一个盛行的代孕医疗旅游市场,在2012年贡献了十几亿美元。[59]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提交了《国家辅助生殖技术(ART)诊所认证、监督和监管指南》草案,并在2005年获得批准。在印度,代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监管的,这使得我们不可能知道发生的交易的确切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儿童的数量。
此外,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政府监管,试管婴儿代孕诊所或者代孕中介机构就没有动力充分保护妊娠代孕妈妈的权利和利益。这也使得妇女权益可能为资本利益而被侵犯。这是因为大多数试管婴儿意愿诊所和代孕中介机构允许自由市场来主导代孕过程,包括代孕妈妈必须遵守的条件,而不考虑她们的权利和合理利益。[62]在印度,许多选择代孕安排的妇女不识字,受教育程度有限,而且对代孕本身如何运作一无所知。[63]此外,为孕育胎儿提供高额回报被认为损害了这些贫困妇女在同意代孕时给予知情同意的能力。自由意志和知情同意的权利不可能适用于极端贫困和教育有限的社会环境。
因此,印度起草了《2016年代孕(监管)法案》。[65]该法案禁止商业代孕,只允许严格要求下进行利他代孕。[66]规定利他代孕中,代孕妈妈只能由年龄在25-35岁之间,是预期父母的"已婚近亲属"进行------尽管 "近亲 "的定义很模糊。[67]2016年法案失效,2019年通过《2019年代孕(监管)法案》重新提出。据报道,截至2020年3月,该法案已获内阁批准,并作了一些修改,正等待总统批准。
相关阅读:印度代孕的限制-印度《2020年代孕监管法案》的变化与进步
综上所述,很明显,印度蓬勃发展的商业代孕行业只是不受监管的商业代孕泛滥的结果,印度政府只是试图纠正其错误。然而,正如在泰国的代孕案例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商业代孕本身,而在于其法规。如果印度将代孕法律执行放在ICMR的指导方针下,或有关知情同意的指导方针下,也许政府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代孕中介机构和试管婴儿医院诊所对代孕妈妈的剥削。
2. 马来西亚可以避免对代孕妈妈的剥削吗?
是可能的,理由有以下四条。
- 第一,我们认为,与印度这样的贫困国家相比,马来西亚不太容易出现剥削妇女的现象。马来西亚的产妇保健比印度更健全,因为2017年马来西亚的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名孕妇中有29人,[69]而印度截至2016年的产妇死亡率为122人。[70]这表明,马来西亚在保护代孕妈妈方面会更加好。
- 第二,马来西亚女性更了解怀孕的情况,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马来西亚,28%的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男性。[71]
- 第三,由于缺乏知情同意是剥削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建议在马来西亚试管婴儿生育诊所实施并强制执行代孕安排的知情同意准则,确保代孕妈妈在知情下做出选择。这种同意必须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并由公正的顾问监督这一过程。[72]
- 第四,必须对预期父母进行合适的筛选,调查是否有犯罪背景和虐待儿童的情况,以确保父母的可信度和背景记录的良好性。[73]
- 因此,尽管必须谨慎处理剥削问题,但它肯定可以得到妥善处理。只要有了适当的机制,马来西亚应该可以允许代孕合法化。
B. 宗教问题/伊斯兰教
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特有的问题,即商业代孕在伊斯兰教法中的地位。虽然有几个宗教禁止代孕的做法,但马来西亚在穆斯林家庭事务方面是由伊斯兰教法具体管理和规范的。因此,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斯兰教对代孕的看法。在伊斯兰教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
- 第一,马来西亚联邦领土的穆夫提认为,所有类型的代孕都是被禁止的。这种禁止是由于担心孩子的血统和父母的监护权被扭曲,造成法律和宗教问题。[74]。
- 第二,一个男人让一个不是他合法妻子的女人怀孕是违反古兰经的。[75]
第二种意见:
禁止传统代孕,但允许妊娠代孕。因为有可能丈夫和妻子都是婴儿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生父母,只是利用了代孕妈妈的子宫。马来西亚国家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采用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只要精子和卵子属于已婚夫妇,妊娠代孕就是被允许的。尽管如此,即使基于宗教原因禁止商业代孕,它仍然可以对非穆斯林合法化。
C. 监管和执行不力-泰国代孕案例的研究
对妇女的剥削和未能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不是商业代孕的固有产物,而是监管不力的产物。这一点在泰国商业代孕发展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直到2015年,泰国并没有明确禁止商业代孕,但商业代孕在泰国成为一个有利可图且严重缺乏监管的业务。这是因为关于试管婴儿医生执行商业代孕程序资格的规定很少被正确执行。此外,也没有为代孕机构或代孕妈妈制定任何监管法规。[77]泰国医学委员会在1997年和2001年为包括代孕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出台了专业准则,但这些准则并没有立法效力,也没有什么动力来监管这样一个高利润的行业。
1. Baby Gammy案
2015年的Baby Gammy案后,对商业代孕的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泰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污点。首先是Baby Gammy案中,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付钱给一名年轻的泰国代孕妈妈,让她怀上双胞胎。然而,这对夫妇只把双胞胎中健康的女孩带回家,把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双胞胎兄弟Gammy留在泰国与代孕妈妈在一起。这个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有人指责这对澳大利亚夫妇抛弃了他们的儿子,但他们否认了这一点。据这对预期父母说,他们在怀孕后期才发现伽米将出生时患有唐氏综合症。这对夫妇承认,如果在怀孕阶段可以安全的减胎,他们可能会决定终止妊娠。在Baby Gammy案中,代孕妈妈和预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差,预期父母也没有得到有关怀孕的最新信息。如果代孕监管法律中,规定代孕合同包括向预期父母提供代孕妈妈怀孕期间常规的最新信息,以及必须在双方之间建立联系,那么代孕妈妈被迫留下婴儿的结果是可以避免的。
2. 婴儿工厂案-日本男子Mistutoki Shigeta在泰国代孕16个婴儿案
2014年,泰国警方发现一名24岁的日本男子Mistutoki Shigeta通过11名泰国代孕妈妈生下了16个孩子---"至少有16个婴儿的父亲"。随后,Mistutoki Shigeta因进行人口贩运而受到调查。遗憾的是,在泰国代孕妈妈放弃了她们的母亲权利之后,Shigeta获得了这些婴儿的唯一监护权,这体现了泰国关于代孕的宽松和监管不当的法律。然而,有利的一面是,此案导致了泰国禁止了对外国人商业代孕服务,收紧了关于商业代孕的法律。
这些事件和由此产生的公愤非常清楚地表明,泰国需要对商业代孕进行更好的执法和监管。这导致了泰国对商业代孕的打击,主要是通过自2004年以来存在的代孕监管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在2015年被更新,泰国代孕法律草案正式生效。[81]然而,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被颁布。[82]泰国代孕案例研究表明,必须对所有代孕相关方实施适当的法规和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在向预期父母提供有关怀孕的必要信息方面。
D. 父母权利-关于美国代孕案例研究
父母权利在任何代孕安排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马来西亚要通过一个法律框架来使代孕合法化,包括商业代孕,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父母权利和父母责任的分配从根本上影响着未成年人的福利。[83]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明确规定,以适当的父母权利分配的机制来确保所有各方的最佳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前的许多代孕案例研究中,谁将获得新生儿的监护权是父母与儿童亲权的关键。[84]在美国,尽管各州的代孕法规各不相同,[85]但在父母权利方面有明确的法律框架。
相关阅读:什么是Pre-birth Order(出生前亲子令,PBO)-美国代孕法律流程详解
在美国,1973年的《统一亲子关系法》(UPA 1973)[86]已被应用于商业代孕中,提供了一个"司法途径确定亲子关系的综合方案"。[87]尽管该法起源于加利福尼亚的亲权法律,但该法已被美国其他11个州采用。[88]一个重要条款是UPA 1973的S.7633,授权法院发出出生前亲子关系令(Pre-birth Order,即“PBO”)、这是一个法院下达命令的判决,在代孕中将合法父母身份指定给预期父母。出生前亲子关系令确认了预期父母与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的合法亲子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通过出生前的法院命令确定父母权利,可以让所有各方在代孕安排开始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并确保在孩子出生时没有法律冲突。
相关阅读:合法代孕需要哪些法律手续?在美国代孕的法律程序流程
此外,从判例法来看,199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Johnson诉Calvert一案及其意向性亲子关系理论已经成为加州大规模商业代孕行业的基础。达成妊娠代孕安排的妇女并不是在行使她自己的生育权利来做出生育选择;她是同意提供一种必要的、深刻的、重要的服务,但(根据定义)并不期望她会把所生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这表明法院非常赞成预期父母有权获得孩子的监护权。
然而,一年后在Re Marriage of Moschetta案中,[92]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对传统代孕做出了明确的阐述。法院认为,代孕妈妈也是亲生母亲,她应该有权监护婴儿,因为'生物联系就是命运'。因此,选择传统代孕的夫妇不能保证他们的意图会在法庭上得到尊重和承认。 尽管如此,应该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的。因此,在传统代孕安排中,任何监护权的争议仍然是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逐案决定,没有标准的做法。总之,美国代孕中,父母权利授予模式足以保护儿童的福利。
讨论 - 代孕的法律框架
应前面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代孕法律框架,使马来西亚的商业代孕合法化。
- 预期父母必须是已婚夫妇。
- 代孕妈妈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 生育诊所的准则,特别是代孕妈妈的知情同意。
- 预期父母的适合性筛选(例如有没有虐待儿童历史和犯罪史)。
- 预期父母必须经常从生育诊所收到有关代孕妈妈怀孕的最新信息。
- 法院必须为每一个商业代孕安排做出“出生前亲子关系令”(Pre-birth Order, PBO)。
关于马来西亚代孕合法化的结论
商业代孕在马来西亚的出现是必然的。代孕不只是政府、生育诊所和代孕妈妈的生意,而是对妇女平权和生育权这一原则的行使。虽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我们将商业代孕合法化,但只要我们从所发生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并向上述国家学习,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可以在商业代孕行业走上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Badrul Alias, Nuralia Dayana Binti Supiyan, 'Awatif Faqihah Binti Mohd Nazri, Fatin Nurwinnie, and Yang Solehah binti Abd Aziz.
编辑:Nur Zarisa。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马来亚大学法律评论》及其所属机构的观点。
脚注/引用:
[1] Krause, F, and Boldt, J, Care in Healthcare. SpringerLink. 1 May, 2020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 ... -61291-1#about>.
[2]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医学委员会,辅助生殖。马来西亚医学委员会的指导方针。2006年11月14日,2020年5月4日<http://mmc.moh.gov.my/images/con ... eproduction.pdf>。
[3] *在体外受精(IVF)的形式中,用预期父母提供的配子创造胚胎,并转移到代孕妈妈的子宫中,以便怀孕并最终分娩婴儿。
[4] Bromfield, N.F和Rotabi, K.S,"全球代孕、剥削、人权和国际私法-务实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全球社会福利1(2014):123-135。2020年4月30日 <https://doi.org/10.1007/s40609-014-0019-4>。
[5] Bhatia, K, et al. (2009). "代孕:临床医生的基本指南"。妇产科医生》。11 (2009): 49-54. 2020年5月1日 <doi:10.1576/toag.11.1.49.27468. issn 1744-4667>。
[6] 见脚注4。
[7] Smolin, D M, "The One 100 Thousand Dollar Baby: 一个新的美国出口的意识形态根源" Cumberland Law Review. 1 (2019): 4 May 2020 < https://advance-lexis-com.ezprox ... ontext=1522468>.
[8] Ramskold, L A H, and Posner, M P, "Commercial Surrogacy: How Provisions Of Monetary Remuneration and Pow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Prevent Exploitation Of Gestational Surrogate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9 (2013): 397-402. 2020年5月5日<https://www.jstor.org/stable/43282765>。
[9] 马来西亚总检察院。<http://www.agc.gov.my/agcportal/ ... GNmTGFJdlNIdz09>网站于2020年5月1日。
[10] Bromfiel, N F, "Surrogac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Experiences In My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9 (2016): 192-217. 2020年5月5日<https://www.jstor.org/stable/10.2307/90011864>。
[11] Johnson v. Calvert, 5 Cal. 4th 84.
[12] 见脚注8;"有偿代孕应该被允许还是被禁止?" 康奈尔法律学院出版物(2017):1551。2020年5月6日<http://scholarship.law.cornell.edu/facpub/1551>。
[1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通过,993 U.N.T.S。
[1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2)条。23(2), adopted Dec. 16, 1966, 999 U.N.T.S. 171
[15] Karen Noelia Llantoy Huamán v. Peru, Communication No. 1153/2003, U.N. Doc. CCPR/C/85/D/1153/2003(2005)。
[16] Aassve, A, et al., "Institutional Change, Happiness, and Fertil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2015): 749-765. 2020年5月3日<doi: 10.1093/esr/jcv073>。
[17] Kealey v Berezowski (1996) 136 DLR (4th) 708。
[18] 见脚注2。
[19] 《世界人权宣言》,第16.1条。
[20]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RC),CCPR第19号一般性意见:第23条(家庭)保护家庭、婚姻权和配偶平等,1990年7月27日,<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5139bd74.html>网站2020年5月14日访问。
[21] 见脚注19,第25.2条。
[22] 见脚注4。
[23] Davies, Iwan. "生育合同"。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1 (1985): 61-65. 2020年5月1日。<www.jstor.org/stable/27716353>。
[24] 见脚注23。
[25] Re C (A Minor) 1985。
[26] Brahams, D. "英国对商业代孕的仓促禁令"。黑斯廷斯中心报告17(1987):16-19。2020年5月1日<www.jstor.org/stable/3562435>。
[27] 见脚注26。
[28] Gamble, N, "我们时代的儿童"。家庭法杂志1(2008):11-13。2020年5月4日<https://www.ngalaw.co.uk/uploads/docs/538c9764e9053.pdf>。
[29] 见脚注26。
[30] Alghrani, A, and Griffiths, D, "The regulation of surrog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ase for reform". 儿童和家庭法季刊》29(2017):165-186。2020年5月2日<http://sro.sussex.ac.uk/id/eprint/68402/>。
[31] 见脚注30,第166页。
[32] 见脚注30。
[33] 见脚注30。
[34] 见脚注26。
[35] 见脚注30。
[36] Jackson, E, "英国法律和国际商业代孕:'合理的对立面'---医学法律与伦理杂志》4(2016):197-214。1 May 2020 < doi.org.10.7590/221354016X14803383336806>。
[37] 见脚注36。
[38] 见脚注36。
[39] 见脚注36。
[40] 见脚注26。
[41] 见脚注30。
[42] 见脚注30。
[43] 见脚注30。
[44] 见脚注30。
[45] 见脚注30,第174-176页。
[46] 见脚注28。
[47] 见脚注28。
[48] 见脚注36。
[49] Pascoe, J, "Sleepwalk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 代孕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新加坡法学院学报》30(2018):455-483。2020年4月30日 <https://journalsonline.academypu ... Law-Journal-Special Issue/eArchive/ctl/eFirstSALPDFJournalView/mid/513/ArticleId/1302/Citation/JournalsOnlinePDF>。
[50] 见脚注1。
[51] Philippa Mary Trowse, Exploitation and Harm in the Context of Indian Commercial Surrogate Women, (Thesis, LLB (QUT); LLM (QU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8)。)
[52] Palattiyil, G B, "全球化和跨国界生殖服务 印度代孕对社会工作的伦理影响》,《国际社会工作》53(2010):686-700。2020年5月4日<https://doi.org/10.1177%2F0020872810372157>。
[53] 商业化的代孕剥削了妇女,2019年6月14日,全国妇女组织。2020年5月3日。<https://now.org/media-center/pre ... exploits-women/>。
[54] Fenton-Glynn, C, "Surrogacy: 为什么世界需要'出售'婴儿的规则》BBC新闻,2020年5月2日<https://www.bbc.com/news/health-47826356>。
[55] 见脚注55。
[56] 见脚注4。
[57] Kristine Schanbacher,"印度的妊娠代孕市场。对贫穷、未受教育的妇女的剥削",《黑斯廷斯妇女法律杂志》25期(2014年):201-220 <https://repository.uchastings.edu/hwlj/vol25/iss2/>。
[58] Rotabi, K. S., et al., "Regulating Commercial Global Surrogacy: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Work, 2 (2017): 64-73 <https://doi.org/10.1007/s41134-017-0034-3>.
[59] F. Krause, J. Boldt (eds.), Care in Healthcare,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61291-1_>.
[60] Verma, T. "印度的代孕法律是什么。这里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印度快报》,2020年5月5日<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 ... o-know-4555077/>。
[61] 见脚注4。
[62] 见脚注56。
[63] 见脚注52。
[64] Fasouliotis, S, and Schenker, J, "Social Aspects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5(1999): 26-39。2020年5月2日<https://doi.org/10.1093/humupd/5.1.26>。
[65] "Lok Sabha通过代孕(监管)法案"-印度教在线》,2020年5月6日<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 ... cle28824277.ece>。
[66] 见上文脚注64,1。
[67] Ashna, D, and Warrier, A, "Surrogacy (Regulation) Bill, 2019 Passed by the Lower House of the Indian Parliament", South Asia Journal <http://southasiajournal.net/surr ... an-parliament/>.
[68] Bhandare, N, "The abolition of choice" Livemint, 4 May 2020 <https://www.livemint.com/mint-lo ... 972678261.html>.
[69] 世界银行,(2019年):孕产妇死亡率(模型估计,每10万名活产)--马来西亚。取自<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STA.MMRT?locations=MY>。2020年5月9日。
[7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孕产妇健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办事处。取自<https://www.unicef.org/india/what-we-do/maternal-health>。2020年5月9日。
[71] Morley L, et al., "Managing Modern Malaysia: 高等教育领导层中的女性",Ed., Eggins, H. 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斯普林格。2020年5月9日 < DOI 10.1007/978-319-42436-1>。
[72] 见脚注4。
[73] Smolin, D M, "The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 Baby: 一个新的美国出口的意识形态根源" Cumberland Law Review. 1 (2019): 4 May 2020 < https://advance-lexis-com.ezprox ... ontext=1522468>.
[74] 马来西亚,联邦领土穆夫提。Irsyad Fatwa Series 130: 代孕妈妈的裁决》,2016年9月26日。2020年5月7日 <https://muftiwp.gov.my/en/artike ... urrogate-mother>。
[75] 《古兰经》第23:5节,al-Mu'minun。
[76] Nehaluddin Ahmad博士,"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马来西亚法律的比较层面和分析"《马来亚法律杂志》3(2012):i. 2020年4月19日 <https://advance-lexis-com.ezprox ... context=1522468>。
[77] Zimmerman, A L, "泰国对商业代孕的禁令。Why Thailand Should Regulate, Not Attempt To Eradicate", Brooklyn J. Int'l L. 41 (2016): 917. 4 May 2020 < https://advance-lexis-com.ezprox ... ontext=1522468>.
[78] Whittaker, A, "Merit and money: The situated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surrogacy in Thai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7(2014):100-120。2020年4月25日<https://www.jstor.org/stable/10.3138/ijfab.7.2.100>。
[79] Amanda Meade, "Gammy: Australian Parents Wanted a Refund and Would have Aborted Him", The Guardian (10 Aug,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 ... rome-australia>.
[80] "Mitsutoki Shigeta:'婴儿工厂'的父亲赢得了父权",BBC新闻,2020年4月20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43123658>。
[81] 《泰国代孕丑闻和法律指南》,Ed. Gecker,A, 13 September.2014, Northwest Asian Weekly, 3 May 2020 <http://www.nwasianweekly.com/201 ... scandals-laws/>.
[82] 见脚注77。
[83] 见脚注11。
[84] 见脚注78。
[85] 美国代孕法律地图,Creative Family Connections LLC. <https://www.creativefamilyconnec ... rogacy-law-map/>网站于2020年5月2日访问。
[86] 《家庭法》第3部分《1973年统一亲子关系法》。
[87] K.M.诉E.G., 37 Cal. 4th 130. 4th 130.
[88] Farese. K, "The Bun's in the Oven, Now What? How Pre-Birth Orders Promote Clarity in Surrogacy Law", UC Davis Social Justice Law Review 23 (2019): 2 May 2020 <https://advance-lexis-com.ezprox ... ontext=1522468>.
[89] 见脚注87。
[90] 见脚注72。
[91] 见脚注11。
[92] Re Marriage of Moschetta Nos. G013880, G014430.
原文:Surrogate Motherhood, An Economic Choice? An Analysis of Commercial Surrogacy And Its Position In Malaysia,由“91喜来宝”站长翻译整理。
|
|